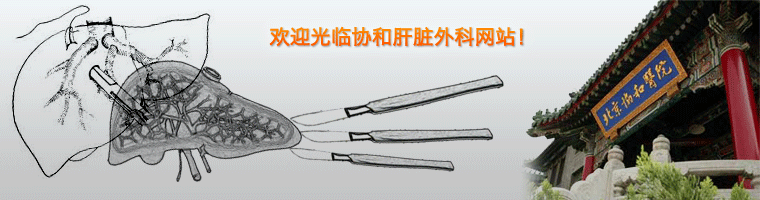病例讨论
病例讨论
危重医学-外科手术相关性感染源自:
第六节. 外科手术相关性感染
一.历史背景
二.相关定义
三.外科患者的常见感染
外科手术部位感染
腹腔内感染
器官特异性感染
外科植入物相关感染
皮肤和软组织的感染
术后医院内感染
脓毒综合征
与职业暴露相关的病原体
四.外科感染与SIRS和MODS的关系
五.外科感染的预防和治疗
感染因素及控制
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六.常见外科感染的病原体
细菌
真菌
病毒
第二章
第六节. 外科手术相关性感染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北京协和医院 外科 毛一雷,徐海峰)
一.历史背景
外科相关感染(surgery related infection),或外科手术相关性感染,是指因外科手术而引起的或需要外科手术处理的感染性病变,这其中包括创伤、手术、烧伤、器械检查和插管后并发的感染。
各种外科手术均存在引起感染的潜在可能,而对感染的治疗也是外科领域固有的一部分。它的进步与微生物学和消毒灭菌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由于现代麻醉学的发展,使外科医生能完成越来越复杂的手术,而术后由于感染造成的并发症和死亡率也越来越低。但直到现在,外科手术相关的感染还是不能完全杜绝。实际上,对外科相关感染的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是近几十年来才逐步发展完善的。
十九世纪一些临床医生和学者的发现对现在外科感染的病因、预防和治疗起了关键的作用。1846年,匈牙利医师Ignaz Semmelweis注意到产褥热造成的死亡率和产妇分娩所处的环境有关,医生们用检查过因产褥热而死的尸体的手再去接触别的产妇,就会使别的产妇也受到传染,因此,他要求所有人接触产妇之前要彻底洗手,这一举措使产褥热的死亡率由大约10%降至1.5%。1861年,根据他的临床观察和实践,Semmelweis出版了有关产褥热的著作。但不幸的是,他的观点不被当时的权威人士所接受。在极端失望中,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于1865年在给一具死于产褥热的尸体做尸检时,故意切下自己的食指并因此身亡。
其后,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为现代微生物学的进展做了有益的工作。他的工作证实,传染性疾病是由某些特定的病原体引起的,这些病原体来自外界而不是被感染者本身。据此,他发明了酿酒时的灭菌方法,并且确定了一些能够感染人类的病原体,包括葡萄球菌、链球菌和肺炎球菌。
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注意到他的接受截肢手术的患者中,有50%因术后感染而死亡。在接受了Pasteur的理论后,他开始用石炭酸(当时用来处理下水道污水的物品)来处理伤口。1867年,他撰文说明,在12位用石炭酸处理伤口的复杂骨折患者中,有11例(其中截肢1例,未截肢10例)恢复良好;另外一例死于与伤口感染无关的原因。很快,他的处理伤口的方法就在欧洲流行开来。
从1878年至1880年,由于当地炭疽热的流行,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发明了培养炭疽杆菌的技术,并且证明了培养出来的炭疽杆菌可以感染健康的动物。由此,他提出确定某种微生物是引起某种疾病的原因所需要的一些实验证据。这些证据包括(1)在每一病例中必须能找到这种微生物;(2)这种微生物必须能分离出来并能生长为纯培养;(3)将此纯培养接种到易感动物时必须能复制该病;(4)在实验性患病动物中必须能找到并分离出这种微生物。他用同样的技术分离出霍乱和结核病的病原体。直到今日,科赫法则仍对我们的工作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个通过开腹手术来治疗感染的方法是阑尾切除术,查尔斯·麦克伯尼(Charles McBurney)在1889年首次报道了用手术治疗阑尾炎的方法;在此之前,阑尾炎是死亡率相当高的疾病。1902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得了阑尾炎,他的医生为他施行了阑尾切除术,使国王最终活了下来。
二十世纪上叶抗生素的发现使外科医生多了一种有效的武器。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爵士在他的实验室里研究导致人体发热的葡萄球菌,由于盖子没有盖好,他发现培养细菌用的琼脂上附了一层青霉菌,这是从楼上的一位研究青霉菌学者的窗口飘落进来的。使弗莱明感到惊讶的是,在青霉菌的近旁,葡萄球菌忽然消失了。这个偶然的发现吸引了他,他设法培养这种霉菌进行多次试验,证明青霉素可以在几小时内将葡萄球菌全部杀死。弗莱明据此发明了葡萄球菌的克星——青霉素。
此后,很多新的病原体(包括很多厌氧菌)被确定,大量的抗生素也被制造出来。研究人员发现,人体的皮肤、胃肠道和其他任何部分都存在着很多微生物,这些微生物是和人类共存的,它们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引起感染。研究人员也发现,需氧菌和厌氧菌可以协同作用,造成严重的软组织和腹腔内感染。这些生存于人体各部分的微生物在正常状态下是不致病的,当外科手术使这些微生物发生易位,进入本来无菌的体腔,或局部和全身免疫力下降时,才会发生感染。
美国医学的奠基人之一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曾经指出,在大部分情况下,患者往往是死于机体对感染的反应,而不是死于感染本身。细胞因子的发现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观察机体对感染的反应,从而了解机体的炎症反应过程。机体对感染的炎症反应可以导致器官功能失调甚至衰竭,预防和治疗感染中的多器官衰竭是现代重症医学和外科感染研究的主要挑战之一。
我国传统医学中,关于外科感染的概念也开始很早。秦汉时候的医学名著《内经》中已有外科“痈疽篇”,当时已经认识到破伤风(伤痉)的发病与创伤受风有关,婴儿破伤风(索痉)与居住潮湿及脐带不洁有关。隋朝巢义方著《诸病源候论》对炭疽的感染途径做了探讨。明朝薛己总结了婴儿破伤风的预防方法,汪机批评了等脓肿自破的错误观点,王肯堂记载一妇人售羊毛引起紫泡疔(炭疽)流行,造成大量死亡的病例,对炭疽的传染途径、局部体征、发病部位、全身症状和预后做了较正确的叙述。祖国传统医学的观点,可以和现代西方医学互相补充。
二.相关定义
病原体入侵机体,机体的免疫系统与之进行对抗,通常有以下几个结果:(1)病原体被机体清除;(2)局限性的感染,通常会导致化脓性改变,这是慢性感染的特点(如皮肤上的疥疮,软组织和器官的脓肿等);(3)局灶性的感染(如蜂窝组织炎、淋巴管炎以及进展型软组织感染等,伴或不伴感染的远处播散,转移性脓肿);(4)系统性全身感染(如菌血症或真菌血症等)。很显然,后者意味着机体的抵抗力在局部的失利,在临床上有更高的致死率,但是在临床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同时,慢性的脓肿也有可能会造成全身的菌血症。
感染包括特定的病原体的入侵和机体对之的炎性反应。在感染的部位通常会发现红、肿、热、痛等经典体征。大部分感染部位都会出现上述临床特点,有的还会出现全身性的改变,如白细胞计数的升高、心跳加快或呼吸急促等。这些全身性的改变是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的表现。
SIRS可以由很多原因引起,包括胰腺炎、多发性外伤、恶性肿瘤、输血反应等,当然也可以由感染引起。由感染引起的SIRS常常表现为脓毒症,如果患者的症状符合SIRS的诊断标准,同时又存在局部或全身感染的证据,则可确认脓毒症。
严重脓毒症是指在脓毒症基础上伴发新出现的器官衰竭。在美国,严重脓毒症是心脏监护病房之外的监护病房中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每年大约有20万患者死于严重脓毒症。而我国的报道则显示,严重脓毒症患者的死亡率约为50%。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评价器官功能不全的指标,即:如果患者存在脓毒症的基础上,需要机械通气支持,出现少尿而且对液体治疗没有反应,或者需血管活性药物来纠正低血压,这时应该考虑严重脓毒症的诊断;如果患者出现急性循环衰竭,主要表现为没有其他明显原因而出现持续的低血压(收缩压<90mmHg),对液体治疗反应不佳,这种状态称为感染性休克(septic shock)。感染性休克是感染造成的最严重的临床表现,大约40%的严重脓毒症患者会发展为感染性休克,一旦出现这些情况,死亡率非常高,可达60%~80%。国内有些报道表明,感染性休克患者的死亡率可达70%以上。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ction syndrome,MODS)是指在严重创伤、烧伤、大手术、休克、感染等过程中,同时或相继出现两个以上的器官损害以至衰竭的综合征,或出现与原发病损无直接关系的序贯或同时发生的多发器官功能障碍。MODS的概念产生于历次人类较大规模的战争中,形成于70年代初期,1977年Eiseman和Fry提出多器官衰竭(multiple organ failue, MOF)和多系统器官衰竭(multiple system organ failure,MSOF)的概念,1991年美国胸科医师学会和危重病急救医学学会(ACCP/SCCM)提议将MOF和MOSF更名为MODS。诊断MODS目前无统一标准,主要根据心、肝、肺、肾、胃肠道、凝血系统等的功能来评价。
三.外科患者的常见感染
(一)外科手术部位感染
外科手术部位的感染是指进行外科操作时所暴露的组织、器官或体腔的感染。手术部位感染可分为切口感染和器官/体腔感染,前者又可分为浅部(局限于皮肤和皮下组织)和深部切口感染。外科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主要跟三个因素相关:(1)术中伤口部位病原体的浓度;(2)手术持续时间的长短;(3)患者身体的因素,包括高龄,免疫抑制,肥胖,糖尿病,慢性炎症,营养不良,周围血管疾病,贫血,接触辐射史,慢性皮肤病,携带细菌状态(如葡萄球菌),近期手术史等。如果外科手术的切口出现了脓液,则肯定发生了感染,这时外科医师根据判断往往会将切口敞开。
表2-6-1 手术部位感染的一些危险因素
患者因素
高龄
免疫抑制
肥胖
糖尿病
慢性炎症
营养不良
周围血管疾病
贫血
接触辐射史
慢性皮肤病
携带细菌状态(如葡萄球菌)
近期手术史 局部因素
术区皮肤准备不洁
手术器械污染
不合理的抗生素的应用
手术时间过长
局部组织坏死
体温过低时的组织缺氧
病原体因素
住院时间过长,导致院内感染
病原体在体内分泌毒素
囊肿形成,不利清创
外科伤口可以按照手术时伤口被污染的情况进行分类(表2-6-2)。清洁伤口(I类伤口)指没有污染存在的伤口,这类手术的操作不进入含有病原体的空腔脏器(如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生殖道),只有皮肤上的微生物存在潜在的污染的可能。这类伤口还有个亚类(称为I亚类伤口),指需要放入假体材料(如网片、瓣膜等)的类似切口。介于清洁和污染之间的伤口(II类伤口)指术中操作需要进入空腔脏器(如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生殖道)的伤口,这些空腔脏器均含有一些定殖的微生物,需要经过严格的术前准备,而且术中不能有空腔脏器内容物的明显外溢。污染伤口(III类伤口)包括早期得到处理的开放的外伤性伤口;从有菌部位进入无菌部位的伤口(如紧急情况下直接的心脏按压);被大量空腔脏器内容物污染的伤口,以及在已经有炎症但没有化脓的部位所作的切口。污秽伤口(IV类伤口)包括开放的外伤性伤口不能得到早期处理,产生了组织坏死;存在明确化脓性感染的伤口;以及空腔脏器的穿孔伴随大量内容物的溢出。手术部位感染的病原体与原先患者作为宿主的病原体相关。I类伤口如发生感染,则病原体很可能来自皮肤,II类伤口(如结肠部分切除手术的伤口)发生感染,其病原体则可能来自结肠内微生物或/和皮肤。
表2-6-2 伤口分类,代表性手术,以及相对感染几率
伤口分类
手术
感染几率
清洁(I类)
疝修补
乳腺活检
1.0%~5.4%
沾染(II类)
胆囊切除
胃肠道部分切除
2.1%~9.5%
污染(III类)
腹部锐器伤
肠梗阻时的肠切除
3.4%~13.2%
污秽(IV类)
肠道憩室穿孔
软组织坏死合并感染
3.1%~12.8%
外科手术部位感染在临床上比较常见,不但会增加患者经济负担、生活的不便和情绪的不满,偶尔还会造成患者死亡。因此,外科医师总是尽力避免手术部位感染。抗生素的合理应用可以降低一些手术伤口的感染几率,现在普遍认为,对于I亚类,II,III,IV类伤口,至少在外科手术刚开始之前,应该应用一次抗生素。对于那些院内感染几率较高的患者,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是否有效尚待证明。应用抗生素能否降低清洁伤口的感染几率存在争议,但是清洁伤口也有潜在的感染的风险,故笔者主张应该在手术刚开始之前应用一次抗生素。
伤口的外科处理方式也会对感染造成影响。对于一个相对健康的个体,I类和II类伤口可以行一期缝合,而III类和IV类伤口的一期缝合会造成比较高的切口感染几率(约25%~50%)。对于IV类伤口,伤口的浅层应该敞开,以期获得二期愈合。现在有文献表明,选择性的延时的一期缝合也可以降低这些伤口感染的几率。应用有效的、针对性的抗生素能降低III类和IV类伤口感染的几率。研究表明,对于穿孔或坏疽性阑尾炎,在手术切除阑尾后一期缝合,同时应用覆盖厌氧菌和需氧菌的抗生素,发生伤口感染的几率大约为3%~4%。
目前有些学者正在研究进一步降低外科伤口感染率的方法。一些文献报道了血糖水平过高对白细胞功能造成的不利影响,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后,高血糖水平会增加伤口感染率。因此,临床医师应该将患者的血糖控制于合适的范围之内。
有人曾经研究过术中吸入的氧气量和伤口的预热与伤口感染率之间的关系,术中吸入氧气量增加可能会降低结直肠手术术后感染率,而对切口部位预热30分钟后再进行手术,也可能使伤口感染率有所下降。但是,目前还很难对此作出最后判断。
临床实践表明,单独的切开引流而不应用抗生素,对于外科伤口的感染是有效的。如果确定有严重的蜂窝组织炎,或并发了脓毒综合征,抗生素的使用则是必要的。感染伤口敞开后,要注意每天更换敷料两次。局部应用抗生素的效果尚未证实,但有个案报道显示对于一些非常规的复杂伤口也许有效果。
(二)腹腔内感染
腹腔被病原体污染称为腹膜炎或腹腔内感染,可以按病因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病原体(往往是细菌)从远处通过血行播散至腹腔,或者直接来自腹腔,就会造成原发性腹膜炎。这种情况多见于有大量腹水,或者因为肾功能衰竭而进行腹膜透析的患者。这种感染往往由单一的细菌造成,而且很少需要外科的处理。如果存在上述表2-6-1所提到的危险因素;体格检查发现广泛的压痛和肌紧张,而没有固定的压痛点;立位腹平片排除气腹的存在;腹水标本白细胞数超过105/L,革兰氏染色为单一形态,那么,原发性腹膜炎的诊断基本就可以成立了。如果做腹水标本的病原学培养,可能出现的病原体有大肠杆菌、肺炎克雷白杆菌、肺炎球菌、葡萄球菌、肠球菌、白色念珠菌等等。治疗上主要是应用敏感抗生素,疗程往往需要用至2~3周。对于腹膜透析的患者,如果出现了反复发作的原发性腹膜炎,为了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可以考虑将腹透导管或动静脉分流用的人工血管取出。
腹腔内脏器的严重感染和穿孔则会造成继发性腹膜炎,如阑尾炎、胃肠道任何部位的穿孔,或憩室炎等。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是结肠穿孔,大量结肠内容物的流出会造成腹腔的感染。治疗上包括切除感染器官,对坏死组织进行彻底清创,以及应用能够覆盖厌氧菌和需氧菌的抗生素等。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外科手术才能取得明确的诊断和病原学证据,因此应用相对广谱的抗生素是必要的,而且根据情况可以联合应用抗生素。有效的去除原发病灶和合理应用抗生素可以使继发性腹膜炎的死亡率控制在大约5%~6%;如果不能控制原发病灶,死亡率则有可能超过40%。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清除原发病灶和合理应用抗生素可以使继发性腹膜炎治疗的有效率达70%~90%。如果应用上述两种方法后仍不能控制病情,患者就会出现腹腔脓肿。胃肠道吻合口瘘会造成手术后的腹腔感染和腹膜炎,这种腹膜炎往往比较顽固,对于存在免疫抑制的患者尤其困难。细菌培养会发现粪肠球菌、表皮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绿脓杆菌等,而且往往是几种细菌同时存在。即使应用有效的抗生素后,这类患者的死亡率也往往会超过50%。
以往的腹腔脓肿需要外科手术清创引流。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大部分这类脓肿可以由CT做出诊断,并行经皮穿刺引流。如果存在下面这些情况,则仍需要外科手术处理:(1)、存在多个脓肿,穿刺效果不佳;(2)、脓肿距离重要脏器非常近,经皮穿刺可能会造成重要脏器的损伤;(3)、一些比较明确的病因,如肠瘘等。抗生素应用的必要性和置管引流的时间长短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从临床经验上来看,应用覆盖厌氧菌和需氧菌的抗生素,持续时间3~7天是比较合理的;笔者认为如果脓肿已经变小消失,每日引流量不超过5~10ml,没有明确的感染源(如肠瘘)的存在,患者的临床症状逐渐缓解,则引流管可以经1~2次退管后拔除。
(三)器官特异性感染
肝脓肿现在在城市居民的患者中越来越少见,西方国家则更少,每10万住院患者中只有大约15例肝脓肿患者。细菌性肝脓肿是最常见的,约占肝脓肿总数的80%,寄生虫性肝脓肿和真菌性肝脓肿大约各占10%。以前,细菌性肝脓肿往往由阑尾炎或消化道炎症造成的门静脉炎所引起。而现在,由胆道原因引起的细菌性肝脓肿逐渐成为主要病因,但仍然有约50%的患者找不到明确的病因。在文献报道中,最常见的需氧菌包括大肠杆菌、肺炎克雷白杆菌、肠球菌、绿脓杆菌等,最常见的厌氧菌有厌氧的链球菌、梭状菌和白色念珠菌等,而白色念珠菌是引起真菌性肝脓肿的最主要的病原体。比较小的(<1cm)、多发的肝脓肿应当取得标本进行培养,需要应用抗生素4~6周。大的肝脓肿往往需要经皮穿刺引流。脾脓肿相当的少见,处理原则与肝脓肿类似。反复发作的肝脓肿或脾脓肿往往需要手术。
在出血坏死性胰腺炎的患者中,大约10%~15%会发生继发性的胰腺感染(如胰腺坏死或胰腺脓肿)。对于此类疾病的感染阶段,Bradley和Allen二人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们注意到,对于胰腺感染后坏死,进行反复的清创术会显著改善治疗效果。目前,对于急性重症胰腺炎感染期的患者,需要进行胰腺增强CT薄扫(每3mm一个层面),以帮助确定胰腺坏死的范围,并在ICU进行密切的监护,动态观察胰腺坏死的范围。
继发性胰腺感染经常在胰腺炎发作几周后出现,有证据表明,经验性应用抗生素可以降低继发性胰腺感染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几项随机的前瞻试验表明,应用碳青霉烯类和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可以降低胰腺感染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早期应用肠内营养(将鼻空肠管远端放至超过Treitz韧带的位置)也可以降低胰腺感染坏死的几率,这可能与肠内营养可以降低肠道菌群易位的发生有关。最近的指南支持肠内营养的应用,如果鼻饲营养不足以满足患者的能量需要,则可以补充肠外营养。
对于胰腺炎的患者,经治疗后如果全身炎性反应(包括发热、WBC计数升高或器官功能障碍)不能得到缓解;或者症状明显缓解后两到三周出现脓毒症的症状,都要怀疑继发性胰腺感染的可能。CT引导下穿刺引流,引流液标本的革兰氏染色和培养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革兰氏染色或细菌培养阳性,并从CT上能看到胰腺内的气体,都是外科手术治疗的指征。
继发性胰腺感染外科手术的目的是去除感染的炎性病灶,术中应该放置鼻空场管、胃造瘘管,必要时还可以切除胆囊,做胆管引流,或做空肠造瘘术。外科医师应该明确多次开腹清创的可能性,直到坏死和化脓组织完全消失形成肉芽组织为止。大约有20%~25%的患者会发生胃肠道瘘,其中一部分可以自愈,如果不能自愈,可以待胰腺的问题解决之后行手术修补。
感染性心内膜炎是心脏外科常见而诊治仍较困难的疾病。近年来由于采用预防性抗生素治疗,感染性心内膜炎发生率已降至2.8%~3.7%。感染性心内膜炎在活动期急诊手术的死亡率、术后并发症和复发率均较稳定期手术明显增高,故一般应在使用大剂量敏感抗生素积极治疗6周、感染及心力衰竭得以控制和纠正后施行手术。但如果药物治疗难以控制,并出现心功能进行性下降,此时应果断施行手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围术期处理除加强心肺功能及全身状况支持外,尤应强调对术后感染复发的有效控制。对心肺功能的支持强调良好的术前准备、合理把握手术时机、术中保护心肺功能、术后适当延长呼吸机辅助时间和维持良好的循环功能。术后强调联合应用敏感抗生素6周,防治感染性心内膜炎复发,同时要预防真菌感染、加强全身营养支持、去除原发感染灶。
(四)外科植入物相关感染
自1953年Voorhees首次将涤纶人工血管应用于腹主动脉移植后,各种人工血管已广泛应用于全身各部位,挽救了大量血管疾病病人的肢体及生命。随着人工血管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由此出现的并发症如吻合口出血、吻合口假性动脉瘤、人工血管内血栓形成及人工血管感染等也日益成为血管外科医生共同关注的问题。其中在众多并发症中,又以人工血管感染最为严重,不仅导致手术失败还可导致截肢致残甚至死亡。有文献报道,主髂人工血管感染的病死率可达25%~88%,下肢人工血管感染的病死率<22%,但其截肢率可高达79%。对于不同部位、不同病原菌所造成的感染处理方法不尽相同,传统的方法包括局部清创、切除感染的人工血管以及经解剖外途径血管重建。为了预防人工血管植入物感染,已开发和研制具有抗感染活性的人工血管植入物,其中最主要的是抗生素载药人工血管植入物的研制。抗生素通过适当的方式载至血管植入物使其具血抗感染活性,从而克服原人工血管植入物的缺陷。这些研究正在进行和逐步完善之中。
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并发感染性心内膜炎是心脏外科较为常见而又治疗棘手的疾病之一。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早期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发生率为2%~4%,死亡率较高,达50%~80%。经内科治疗效果不佳、有瓣周漏及赘生物者,应尽早手术治疗。该病临床表现多样化,行人工瓣膜置换术后有发热表现应警惕有发生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可能。彩色超声心动图在诊断上有重要价值,它能清晰辨认瓣周赘生物、瓣环脓肿和人工瓣瓣周漏。外科手术是治疗该病的重要措施。手术的关键是彻底清除感染的组织,这是避免术后再发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关键。葡萄球菌感染因其毒力强、有耐药性,内科治疗较难控制,应尽早手术治疗,术后死亡率也较高,因此,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发生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应早期诊断、适时手术,内、外科联合治疗是成功的关键,延误手术时机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对人工关节手术来说,感染无疑是最为严重的并发症。如何有效地控制感染,保持术后关节的功能,为将来的翻修手术创造良好的条件,已经成为临床工作中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加拿大温哥华总医院的Duncan于二十世纪90年代初创立了PROSTALAC方法,即使用含有抗生素的骨水泥假体对人工关节术后感染进行二期翻修。手术的第一步是取出关节内所有假体,对感染的关节进行一期彻底清创,然后将含有抗生素的骨水泥植入关节间隙,使之成为一种临时性的功能性假体;第二步是等待感染控制后,二期手术取出PROSTALAC,并最终植入正式的全关节翻修假体。此方法已被临床证明具有很高的成功率。PROSTALAC二期翻修手术最大限度地根除了感染,成功地保全并重建了具有良好活动范围和功能的人工关节,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避免了难以接受的关节切除成形术、关节融合术甚至更糟糕的截肢术的施行,为治疗关节置换术后感染找到了一种常规有效的方法。
(五)皮肤和软组织感染
皮肤和软组织感染可以根据是否需要外科手术治疗来分类。例如,对于浅表的皮肤和皮下组织的感染(如蜂窝组织炎、丹毒、淋巴管炎等),在寻找病原体的同时,单纯的抗生素治疗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通常,临床医师会选择主要针对存在于皮肤的革兰氏阳性菌敏感的抗生素。如果是疥疮,可以自发的破溃引流,或者外科手术切开引流。对于蜂窝组织炎,在外科手术切开引流之后也可同时应用抗生素。
快速进展的软组织感染很少见,也很难确诊,需要及时的外科手术治疗,同时应用抗生素。如果不能及时诊断,死亡率相当高(约80%~100%);即使很快得到确诊,及时切开引流和应用抗生素抗感染,死亡率依然会达到30%~50%。过去对于这类疾病的命名和分类非常混乱,比如快速播散的蜂窝组织炎、气性坏疽、坏死性筋膜炎等。如今,对于这种严重的软组织感染,最好的命名系统应该是包括感染组织的层次(例如:皮肤、浅层软组织、深层软组织和肌肉)和引起感染的病原体的名称。
有些因素使得某些患者比较容易罹患这些类型的感染,这些因素包括高龄、服用免疫抑制药、糖尿病、周围血管疾病等,或者同时具备其中几点。这些患者软组织内的血供(或携氧量)低于正常,再加上病原体的侵袭,很可能成为软组织感染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也曾经有健康人群受链球菌侵袭造成快速进展的软组织感染的报道。
在病程开始阶段,这种严重的软组织感染的诊断要靠临床上的症状群来确定,但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出现类似的症状。临床上经常见到这些患者出现脓毒症或感染性休克却找不出任何原因。感染灶常常会沿着四肢、会阴、躯干的顺序蔓延。对这样的患者,要进行仔细的体格检查,以期发现感染灶的所在;有可能会看见皮肤出现灰色浑浊的脓苔样改变,或出现水泡、皮肤变成青铜色调、张力增加等等。患者经常会主诉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最明显,这往往是感染灶存在的地方。如果患者有了以上表现,应该马上进行外科干预,需要暴露感染灶,而且要在直视下将深层的受感染侵袭的组织(包括深层软组织、筋膜以及下面的肌肉)进行放射状的切开。由于此时放射学检查会耽误外科手术的时机,而且经常会混淆临床思路,因此,只有当患者的症状不是很重的时候,才会考虑行X线或CT等放射学检查。有时外科医师为了彻底清除感染组织,往往会选择截肢手术,造成患者的残疾;但是,如果手术不彻底的话,术后感染和死亡率都会增加。
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对受感染的组织液进行培养,对病原体进行革兰氏染色。选择的抗生素要能覆盖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厌氧菌和需氧菌,如万古霉素和碳青霉烯类联用;为了针对梭状芽孢杆菌,还应用联用青霉素G 16,000~20,000U/d。大约有70%~80%的病例的感染源不止一种病原体,剩下的部分由单一的病原体引起,如绿脓杆菌、梭状芽孢杆菌、化脓性链球菌等等。这些感染的病原谱有些类似于继发性细菌性腹膜炎,但不同的是革兰氏阳性球菌更多见一些。如果治疗效果不好,疾病继续进展,大部分患者很可能需要不止一次进手术室。一旦发现感染灶没有得到很好控制,很可能需要彻底的清创和切除更多的组织。而抗生素的应用应该根据培养和药敏的结果来调整,尤其是对于单一病原体引起的软组织感染。
(六)术后医院内感染
院内感染(nosocomial infection)又称之为医院获得性感染,定义是病人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染,住院期获得的感染而出院后才发病者也作医院内感染计。反之,住院前获得的感染不属于此范畴。大多数是由潜在致病微生物引起的,它们多定居在机体某个部位,常见于口咽部和消化道,平时并不引起疾病。常见致病菌多为高度耐药的细菌,如肠杆菌属、沙雷氏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的菌株、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多重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等,而社区(community)感染也称为社区获得性感染,常见致病菌为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克雷伯菌、葡萄球菌、链球菌和厌氧菌等。
医院内感染分为交叉感染与自身感染。交叉感染包括病人之间接触感染,医护人员的接触感染、医疗器械接触感染。自身感染又称为内源性感染。包括当人体受外来细菌侵袭、机体患病、创伤及外科大手术的情况下,正常菌群导致感染性疾病,也称机会感染。病原体包括:(1)耐药菌株,如耐药大肠杆菌;(2)对一般抗生素不敏感,可能致病的微生物,如念珠菌;(3)低或无致病力细菌,如绿脓杆菌;(4)共生菌,如厌氧菌;(5)原虫与病毒,如巨细胞病毒。除细菌本身对外科院内感染的影响外,人为因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医院内感染管理的总体水平,包括医院内感染管理机构的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监测手段,完备的无菌及消毒设施,细菌室的建立及规范的检测方法,各种抗菌药物的配备,有关人员的专业培训和全体医护人员无菌意识的加强等等。总之,与医疗活动相关的所有环节都可影响感染的发生。第二是病人因素,包括病人的原发病的特点、全身免疫状态、经济条件等,甚至病人和家属在医疗活动中的配合程度,都可影响感染的发生。第三是医生因素,是整个医疗活动的中心。它包括医生的责任心、基础理论知识、基本技能和实际操作水平。这里包括医生的手术技巧和经验,更重要的是无菌意识和临床规范,及对各种抗生素特点的熟悉程度。
外科患者在术后的恢复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院内感染的问题。外科院内感染传播途径是空气、接触、医源及微生物,感染部位以外科伤口、呼吸道、泌尿系统最常见,国内有文献表明感染发生率分别为48.17 %、26.14 %和17.17 %。医院感染在不同外科科室其发生部位差别较大,以创口或创面感染为主的是普通外科、骨外科、烧伤科、肝胆外科,呼吸道感染在神经外科肝胆科、烧伤科的发生率较高,与这些病区的患者病情密切相关,从科室分布看,骨外科、烧伤外科、普通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是医院感染的高发科室。外科院内感染不同于其他科室,感染率高,菌种复杂,耐药菌相对较多,多重感染导致的难治感染发生率也明显高于其它科室。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外科手术伤口感染的情况,而其他类型的院内感染与一些导管放置时间过长有关,如导尿的尿管、机械通气的导管、静脉和动脉插管等等。
小便化验的结果是诊断术后患者泌尿系感染的主要根据。这些患者尿中会出现白细胞、细菌、酯酶等。如果患者有尿路刺激的症状,尿培养细菌>104 CFU/ml就可以确诊泌尿系感染;或者对于没有尿路刺激症状的患者,尿培养细菌>105 CFU/ml也可以确诊。治疗上可以选用对泌尿系感染敏感的抗生素,疗程10~14天,以使尿中中能达到足够的浓度。对于能够活动的术后患者,应该在1~2天内尽早拔除导尿管。
较长的机械通气时间会使肺炎发生的几率增加,其感染源多是医院内存在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常常对很多抗生素都耐药。如果X线显示肺部有一处或多处实变,则可以诊断肺部感染。有时候需要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来获得样本,进行革兰氏染色和培养,以确定病原体,从而选用敏感抗生素。根据患者的氧合和呼吸情况,外科术后患者应该尽快脱离对机械通气的依赖。
住院患者的血管内导管相关感染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很多外科手术的复杂性,越来越多的导管应用于生理监测、血管通路、给药途径和肠外营养。在国内尚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在美国,留置导管中大约有25%会出现细菌培养阳性,大约5%会出现菌血症。穿刺时间过长、急诊条件下穿刺、非无菌条件下操作、以及多腔导管的使用都会使感染的几率增加。
很多发生血管内导管感染的患者在临床上都没有症状,只是血常规中白细胞计数升高。周围血的培养结果与取自导管附近血的培养结果如果都出现同样的病原体,则应该怀疑导管相关感染的可能。如果患者出现下列情况:皮肤明显的化脓性改变;任何病原体导致的脓毒症(已排除其他原因);或者培养出革兰氏阴性菌或真菌的菌血症;则临床医师应该考虑拔除导管。还有一些特定的低毒力的细菌(如表皮葡萄球菌)造成的感染,如果没有其他的感染途径,也需要考虑导管相关性感染,但这种感染通常用抗生素治疗一段时间后就会有明显效果。应用覆有抗生素的导管可以降低细菌定殖的发生率,但是,昂贵的费用使其得不到广泛的应用。在导丝的引导下,定期的更换导管可以使感染率下降,但是却增加了穿刺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临床医师应该慎重地考虑留置导管的必要性,严密地观察可能出现的感染症状,并且尽可能早地拔除导管。预防使用抗生素和抗真菌药物来防止导管相关感染一般来说是没有效果的,也是不恰当的。
(七)脓毒综合征
很多研究表明,严重脓毒综合征(severe sepsis syndrome)患者,很容易并发菌血症或败血症,并造成一系列感染,治疗上经验性应用抗菌治疗,控制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给予营养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治疗菌血症而言,需熟知常见的细菌谱,从而能够凭经验合理地选择抗生素,是至关重要的。回顾性分析表明,合理的治疗可以使患者的死亡率下降2~3倍。近来,对于严重脓毒综合征和感染性休克的患者,一些新的方法被提出,而且被证明有效的。
一些临床试验对针对严重脓毒综合征的药物进行了研究,包括抗内毒素单克隆抗体(MABs),白介素-1ra(IL-1ra)和抗肿瘤坏死因子-α(anti-TNF-α)等,直到最近,也没有发现哪个药物能取得显著的治疗效果。最新的一种药物是drotracogin alpha的活化形式,又被成为Xigris,是一种重组形式的人体活性蛋白C。有研究表明,应用这种药物可以使脓毒综合征患者的总体死亡率下降6%。这种药物有抗血栓、促纤维溶解和抗炎症的作用,但具体的机制尚未阐明,可能同对抗机体的过度炎症反应有关,这种药物显然不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对于脓毒综合征的患者,如果已经确定了其感染源,或者出现至少一个脏器衰竭的患者,则可以考虑使用这种药物,目前的推荐剂量是24ug/(kg·hour),持续用药96小时。如果需要手术治疗,或者出现致命性的出血,应该停止用药。
对于感染性休克的治疗,很多研究人员重新提出了激素的作用。在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早期,研究表明大剂量的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对脓毒症的患者没有效果。最近,有些学者注意到,ICU病房中的感染性休克患者很可能处于肾上腺功能不全的状态,可能需要给这些患者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一些随机对照研究表明,对严重脓毒症患者来说,应用替代剂量的肾上腺皮质激素是有好处的。目前,对于感染性休克的患者,我们通常先进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刺激实验(先测定基础皮质醇水平,然后静脉给予促肾上腺皮质激素250ug,1小时后再测皮质醇水平),如果基础皮质醇水平低于30ug/dl,或者刺激实验后升高小于9ug/dl,则说明患者肾上腺功能不全,这时可给予小剂量的氢化可的松(100mg/8h)。如果患者的肾上腺功能恢复正常,则可停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
(八)与职业暴露相关的病原体
由于临床医师在面对HIV患者时常具备足够的防护心态,因此,HIV由患者传染给外科医师的几率是相当低的。截至2002年全美因职业暴露而在血清中出现HIV抗体的外科医师只有6例,这在所有可能因职业暴露而感染的人员(共195例)中的比例是比较小的,而护士为59例,非外科领域的医师为18例。欧洲的数据表明,外科医师因职业暴露而感染HIV的几率应该在1/20万至1/1000万不等。一些通常的预防措施可以使HIV及其他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的病原体感染医护人员的几率降到最低,这些措施包括:(1)在接触血液或体液的时候应用常规的防护(如佩戴手套和/或护目镜),(2)在接触血液或体液之后立即清洗手和身体其他暴露的皮肤部分,(3)在使用和接触锐器的时候加强注意并妥善放置器具。
如果临床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不慎接触到含HIV的血液或体液(如被抽血针头扎伤等),及时的预防措施对于降低感染率非常重要,为取得最好的效果,最初的措施必须在数小时而不是数天内完成。如果情况比较严重,建议进行二联甚至三联药物疗法。如果患者的HIV感染状态不清楚,建议在做检测的同时开始预防措施,尤其是对于HIV感染高危人群需要这样。
乙型肝炎病毒(HBV)是一种只感染人类的DNA病毒。最初的HBV感染通常是自限性的,但是会转变为慢性携带病毒状态。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大约有30%最终死于肝硬化或肝细胞肝癌。外科医师以及其他所有医护人员都是乙肝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应该接受乙肝疫苗的注射。在接触后的预防措施中,乙肝病毒免疫球蛋白的使用可以保护其中75%的人群免受感染。
丙型肝炎病毒(HCV),以前曾经称之为非甲非乙肝炎病毒,在1980年代后期被确认,是一种RNA病毒。这种病毒可以感染人和黑猩猩。丙肝病毒感染者中,75%~80%会转变为慢性病毒携带者,其中有大约3/4会发展成为慢性肝脏疾病。由于对血源进行检测,丙肝病毒的感染人数在下降。然而在职业中即使出现血液接触,感染丙肝病毒的几率并不大。有文献报道,偶然的针扎伤引起血液出现病毒抗体的几率大约为2%。目前为止,丙肝病毒的疫苗尚未完全研制成功。以黑猩猩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比较早的时候,曾经有作者应用干扰素-α进行治疗,但此药的副作用较大,也未投入实际临床。
四.外科感染与SIRS和MODS的关系
纵观医学发展史,总是对于一组不能解释的病症进行综合和归纳产生了一个新的医学名词或概念,然后逐渐增加对它本身的病理生理的认识、产生新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在临床上,我们发现创伤、烧伤、感染、自身免疫疾病及胰腺炎等均可导致某些相似的全身反应,它们包括发热、白细胞增高、心输出量增加、呼吸加快和全身血管阻力下降等。这些全身性反应并不能说明原发病的性质及解剖定位,只反映原发疾病所致机体内环境紊乱的严重程度。在以往15年中,人们试图将这些临床征象同感染相联系,但发现有些疾病如:闭合伤、胰腺炎等的某些阶段同细菌或病毒的感染并无关系。以上全身反应的程度可以反映出机体受到疾病打击的程度。国际上曾有用脓毒症,脓毒综合征,高代谢脏器衰竭(Hypermetabolism Organ Failure Complex),多脏器功能衰竭等来对这种综合性全身反应进行描述,但显然均不能很好地涵盖或表达这种在ICU死亡病人中占80%的疾病状态。国内作者也曾用“重症病态”、“分解代谢状态”等来描述这种全身的病理改变,似较“感染综合症”等更为全面、合理,然需进一步术语化。
1992年美国胸科医师学院(ACCP)和危重病医学协会(SCCM)将这种全身性反应定名为SIRS,且计划最终将这种状态进行分级(类似肿瘤分级),以指导治疗。开始,SIRS的概念及其涵盖的范围相对较局限和片面,目前逐渐被接受的概念为:SIRS是不同疾病,包括感染性疾病,所引起的全身性的非特异性炎症反应,这种不能很好控制的、不平衡的、或过度的炎症反应是造成脏器损伤的病理基础,进一步发展可能引起多脏器功能障碍。SIRS可从三种病源状态发展而来:(1)严重感染,(2)机体防御屏障破坏后细菌向体内播散,(3)外伤、休克、软组织破坏及其它的非感染因素引起的重度炎症反应。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SIRS同一些炎症介质有密切关系。很多相关的研究正在进行之中,但细胞分子生物水平上的机理尚未完全清晰,故在SIRS病人的治疗方面,包括抗炎症介质治疗,未有很大的突破,离开制定明确的治疗方案、治疗时间和标准还有一段距离。国内同行中对于把各种疾病的全身反应归结成SIRS并作进一步抗炎症介质治疗存在争议,可能主要是因为目前尚未见有效的处理手段而怀疑此术语存在的实际意义。笔者认为,SIRS这个医学专用名称的提出是临床上归结、研究的结果和需要,并非为了名称而名称。只有有了一个一般的归纳,才能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揭示机理、提出处理方案。也只有通过大量的研究才能对新的名词作可能的修改或判断它存在的必要性。
炎症在一般情况下是机体有效的生理性保护性反应,主要表现为局部的红肿热痛,一旦这种反应脱离控制或发展过度,可产生严重的全身性反应,即SIRS。此时这种反应不再是保护性的,而是破坏性的。与此相对应的是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征(Compensetory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CARS),它是体内抑制炎症发展的表现。在机体发生SIRS的同时,CARS也开始发生,二者共同存在。其发展的最终结局取决于二者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决定了病情的转归。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如果以SIRS为主,则可出现休克、细胞凋亡、MODS等危及生命的险象;如果以CARS为主,则可因为免疫系统受抑制而导致顽固感染,同样会危及生命。只有当二者平衡时,才可能维持内环境稳定,逐渐康复。
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主要参与SIRS的炎症介质主要有内毒素(Endotoxin)、TNF-α、IL-1、血小板活化因子(Platelet Activating Factor,PAF)等,还有很多介质,如IL-6、IL-8、INFs、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PGs、血栓烷)、反应性氧族(O2-、NO、ONOO-)、补体(C3、C4)和应激性激素(儿茶酚胺、皮质醇、血管加压素、胰高血糖素及生长激素)等,都参与SIRS的损伤机理,均属于促炎介质。
在引起SIRS的各种原因中,感染是最常见的一类,其中细菌感染尤为常见,并和临床关系密切。一般外科感染多有明确的原因,如手术区域感染、手术切口感染、开放伤口感染和肠间腔隙感染等,比较容易发现,但有时也存在难以寻找的感染灶,且血液中也培养不出细菌,而全身感染症状和体征明显,难以解释。现已证明,内源性肠道细菌易位往往是感染的原因之一,细菌和/或细菌毒素(主要是革兰阴性菌的内毒素)进入淋巴通道和门静脉,进行播散,直接或通过细胞因子(cytokine,CK)介导,刺激肝窦内皮细胞、Kupffer细胞等释放更多的CK等炎症介质,进一步加重SIRS。早在1895年就有报告指出,细菌可通过完整的肠管迁移至腹腔,导致腹膜炎,但对细菌易位的深入了解并引起关注还是近些年的事。细菌易位是由于肠道综合屏障减弱引起,这种肠道屏障的损害同急性危重病期间肠粘膜低灌注,以及再灌注损伤,肠粘膜通透性增加有关,这可造成肠管内细菌和毒素通过粘膜向肠壁的微血管和淋巴管移动。所以肠管本身功能障碍是造成屏障损害的首要原因。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感染及其伴随的SIRS和MODS会越来越重。严重脓毒症导致重度SIRS,大量CK或其它炎症介质如TNF-α、前列腺素E2(PGE2)、血栓素A2等的释放可引发感染性低血压或休克,致器官灌流不足,成为MODS的前奏。其它一些开始时并无细菌参与的急性危重病,如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大面积烧伤、严重开放性损伤等,如果SIRS发展到失控的地步,源于肠道的细菌感染常常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致命的。
对感染的病原和机制有更深的了解,对SIRS和MODS的诊断更明确,必然给临床诊治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途径。除了传统的加强心、肺等生命体征的监护,合理而有效地使用抗生素,维持水电和酸碱平衡,营养支持及代谢调理等措施以外,针对CK和介质的种种调整措施都在研究和试用,主要有净化和拮抗两种方法。净化方法是运用血液过滤技术,清除血液中的炎症介质,拮抗方法是给予CK单克隆抗体或可溶性CK受体及抗CK受体抗体等,这些方法虽初见成效,但问题较多,比如运用血液过滤技术,如何只清除促炎症因子,而适当保留抗炎症因子,又如何恰当地掌握开始和停用的时间以及疗程,以取得最佳效果,目前尚无成熟的经验。又比如各种拮抗剂都是单一靶向拮抗剂,不能制止CK的极联效应,而且只在SIRS开始前用药效果较好,不切合临床实际。总之,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至于采用谷氨酰胺以保护和加强肠粘膜屏障,无论是动物实验,还是临床应用,都已取得较满意效果。
20世纪70年代初,多器官衰竭(MOF)被认识后,人们仿佛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找到了造成死亡的机制,一时备受关注,甚至将MOF称之为70年代综合征,以后由于发现器官功能有可能恢复,只是一时性的功能障碍,遂又改称MODS。现又有人把SIRS说成是90年代综合征,这些课题,从理论到实践仍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
表2-6-3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的诊断标准
一般情况
发热(体温> 38.3℃)
体温过低(体温<36℃)
心率> 90/min
呼吸急促
精神状态改变
明显的水肿或正液体平衡(> 20ml/kg/24 hours)
没有糖尿病而表现出高血糖血症 炎症指标
白细胞升高(WBC> 12,000/mm3)
白细胞降低(WBC< 4,000/mm3)
未成熟粒细胞>10%
血浆C-反应蛋白 > 正常标准2s.d.
血浆降钙素原 > 正常标准2s.d.
血流动力学指标
动脉血压过低(收缩压<90mmHg,平均动脉压<90mmHg,或收缩压降低>40mmHg)
静脉氧饱和度> 70%
心指数>3.5L/min/ m2
器官功能不全指标
动脉血氧不足
急性少尿
肌酐上升
凝血功能异常
肠梗阻
血小板减少
高胆红素血症
组织灌注指标
高乳酸血症
毛细血管灌注下降
五.外科感染的预防和治疗
(一)感染因素及控制
外科的无菌操作是预防中最重要的环节。操作时应尽可能减少组织损伤,及时清除坏死组织、血块和渗出物。术者的熟练程度也很关键。改进手术方式和操作的熟练程度也有利于外科感染的控制,如仔细操作,细致分离,清除异物、血肿和无生机的组织,引流渗血、渗液和脓液等。此外还应重视围手术的各个环节,如滤过空气、层流系统装置、减少手术室参观人员等优化手术室环境的措施;手术器械和敷料的处理;按常规洗手和戴手套;病人术前洗澡、备皮和术野的处理;备皮方法的改进;以及改善病人营养状况及机体条件等。手术时机的选择对于外科感染的控制也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急诊手术的感染率要远大于择期手术。
近年外科感染治疗的进展之一,是外科医师在充分重视手术干预(引流)和抗菌药物治疗的同时,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感染,力图从改善机体状况着手迎接感染的挑战。例如以“免疫调理”的手段降低感染的易感性;以“代谢调理”的手段,如使用环氧酶抑制剂减轻发热和炎症抑制分解代谢;应用生长激素促进蛋白质合成,增强机体对感染的防御能力;加强维护肠道屏障的措施以控制肠道内毒素和细菌易位等,国内都已在临床上开始了有益的尝试,虽然离成熟还相距甚远,却是一条有希望的出路。微创技术的发展也为抗感染治疗增添了新的手段。经内镜置入鼻胆管,内镜下行Oddi括约肌切开,经皮经肝胆道置管或安放支架,都能立即缓解梗阻性胆道感染,使患者得以渡过难关,以便尔后在较好状态下接受决定性手术治疗。B超或CT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使许多膈下脓肿等深在化脓性病灶病人免于手术。
(二)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应用抗生素分预防性和治疗性用药。预防性用药,指患者未发生感染,在围手术期,特别是在手术前,用抗生素预防或减少感染的发生率。
抗生素对手术部位感染的预防作用无可置疑,但并非所有手术都需要。一般的I类即清洁切口,应注意严格的无菌技术及细致的手术操作,大多无需使用抗生素。预防应用抗生素主要适用于II类即沾染伤口及部分污染较轻的III类伤口。已有严重污染的多数III类切口及IV类切口手术,应在手术前即开始治疗性应用抗菌药物,术中及术后继续应用,不列为预防性应用。
对沾染或污染性手术,术前使用抗生素预防手术部位感染是必要的。预防性抗生素的应用是杀灭或抑制手术区来自空气、环境及患者自身的污染细菌。手术结束切口缝合,手术区污染即停止。因此预防性抗生素的作用也仅仅限于这段时间。预防手术部位感染,必须要在整个手术阶段内使手术区域组织内的抗生素浓度超过可能造成感染的细菌的90%最低抑菌浓度(MIC90),因而术前抗生素预防性应用应在手术开始前20~30分钟进行,即在手术麻醉诱导期给药较为合适,可提供手术时组织内有效药物浓度。如所选用抗生素半衰期较短或手术时间长,则应在术中或术后追加一次给药;如术中失血多,则人体血液及组织的抗生素浓度下降,亦需考虑追加用药。手术后才给予抗生素不能起到预防的目的。手术后长时间使用抗生素,如3~6天或更长,并不能进一步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率,这一观点在国际上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但目前国内对围手术期的抗生素使用时机、对不同手术部位的抗生素的选择、以及预防性抗生素的使用时限等方面还有许多误区和争论,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总结。
抗生素的治疗性应用的适应证为:已有严重污染的Ⅲ类及Ⅳ类切口手术(如开放性创伤或消化道穿孔等)。另外对那些具有高度感染危险因素的病人,如高龄、糖尿病、肝硬化、乳糜腹水、过度肥胖或消瘦、营养不良及免疫功能低下者,均应在术前即按经验加大治疗性用药剂量,直到术后或获得培养结果再转为目标性治疗。这种对重症感染病人的经验治疗要按大剂量、广覆盖的原则,即治疗伊始就选用强有力的广谱抗生素,迅速控制外科手术部分感染的最常见菌群,以阻止病情恶化,并及时转变为目标治疗。
上述的抗生素应用策略,近年来在国外防治医院内获得性感染中,尤其是对于SICU病房内外科感染的防治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把经验治疗与目标治疗有机结合,称之为抗生素降阶梯疗法(antimicrobial de-escalation therapy)。有文章指出,在高危感染的治疗中,抗生素起始量不足,带来了病死率和并发症显著增加。初期的广泛覆盖、有力控制后,并适时调整有针对性的用药,既提高了治愈率,降低耐药性,又缩短了住院时间和减轻经济负担,这一原则日益得到广泛认同。
必须清楚的是,对于外科感染,抗生素仅仅是手术和有效引流等的辅助措施。使用抗生素的目的是限制引流后残余的感染,预防切口感染和降低感染对宿主的侵害。
六.常见外科感染的病原体
表2-6-4列出了造成外科患者感染的一些常见的病原体。
(一)细菌
大部分外科感染是由细菌引起的,通常临床检验医师会用革兰氏染色和特殊的培养基来确定各种类别的细菌。革兰氏染色可以快速将细菌分为两类,单纯从颜色上就能区分。除了革兰氏染色外,还有一些特征可以帮助区别细菌,包括形态(可以区分球菌还是杆菌),分化类型[如单个有机体,成对的有机体(双球菌),成簇的有机体(葡萄球菌)或成链的有机体(链球菌)],以及有无孢子等。
革兰氏阳性球菌常常与人体的皮肤共生,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和化脓性葡萄球菌;肠道也存在一些共生菌,如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而这些细菌经常会造成外科患者的感染。外科手术切口的感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皮肤的共生菌引起的;而对于一些服用免疫抑制药物或者有长期慢性病的患者,肠球菌则会造成腹腔内感染(包括尿道感染和菌血症),对于健康的机体来说肠球菌的毒力则比较弱。
很多革兰氏阴性细菌能造成外科患者的感染。常见的种类有大肠杆菌、肺炎克雷白杆菌、粘质沙雷氏菌、醋酸钙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绿脓杆菌)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等。
厌氧菌不能在有氧的环境中生长和分化,这与它们缺少一种过氧化氢酶有关,而这种酶使得生物能够与氧气进行能量交换。厌氧菌在人体的很多部位都是正常存在的,某些特定的部位有特定的厌氧菌。例如,痤疮丙酸杆菌存在于皮肤表面,它所造成的感染以痤疮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人的口咽部和结直肠通常存在大量的厌氧菌。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因结核分枝杆菌造成感染而死亡的人数是当时死亡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因而成为当时最常见的致死原因。现在知道,这种细菌又被称为“抗酸杆菌”,具有抗酸特性的细菌还有诺卡氏菌等。这些细菌往往生长很慢,经常要在培养基中生长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出鉴别,但是现有的DNA分析的技术可以很快得出结论。
由于感染部位不同,外科感染的类型和病原菌分布有明显差异,国内有文献报道,腹腔内感染中,混合性感染占较大比例,以革兰氏阴性杆菌多见,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粪肠球菌是主要的感染菌,这些细菌多为肠道常居菌,表现为条件致病和内源性感染,并呈现多重感染;创面分泌物的感染菌相对单一,混合性感染相对较少,并以革兰氏阳性球菌多见,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主要病原菌。
(二)真菌
外科真菌感染分为两大类 ,一是创面或创口浅部真菌感染,二是深部真菌感染,包括侵入性真菌感染,系统性真菌感染或全身播散性真菌感染。真菌是条件致病菌,一般情况下不致或极少致病,常见致病菌种有白色念珠菌、光滑念珠菌、热带念珠菌、曲霉菌等,常见感染部位为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道。真菌感染的易感因素包括高龄、机械通气、广谱抗生素的应用、术前放化疗、服用免疫抑制药物、长期慢性病以及侵入性治疗等。此外,静脉高营养、深静脉穿刺、留置导尿管及抑酸剂的应用也是真菌感染的诱因。
在引起感染的菌株中,我国以念珠菌最为常见,其次为曲菌、孢子丝母菌和隐球菌等。临床研究表明,白色念珠菌已成为当今外科危重患者感染的致命病原体,真菌感染特别是威胁生命的深部真菌感染日趋受到重视,其发生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在我国由真菌引起的感染占医院感染发生率的9.6%~11.8%,病死率为30%~80%。目前在发达国家,外科ICU病房内对真菌感染的防治已被置于与防治细菌感染同等重要的地位。
随着广谱抗生素的应用,特别是临床上广泛应用三代或以上的头孢菌素及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大多数的细菌受到抑制。一些临床医师不了解抗生素有固有耐药和天然耐药的特征,不能根据细菌对抗生素敏感度变迁选择抗生素;术前预防应用抗生素时间过长或过广;某些抗生素具有直接促进真菌生长及毒力作用,抗生素可使体内常存菌群量减少或菌种改变,促成了真菌的粘附、增殖和扩散。
(三)病毒
由于体积很小,而且必须在细胞内生长,病毒很难在培养基上被培养出来。以前,病毒感染是根据宿主的抗原抗体反应来确认的。生物技术(如聚合酶链反应)的进展使我们可以通过直接测定DNA或RNA来确定病毒的存在。与很多真菌感染类似的是,外科患者的病毒感染常见于免疫抑制的人群,尤其是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后服用抗排异药物的患者。常见的一些病毒包括巨细胞病毒、EB病毒、单纯疱疹病毒、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等。外科医师要对乙型及丙型肝炎病毒、HIV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些病毒同时也可以传染给医护人员。
表2-6-4 外科患者感染常见的病原体
革兰氏阳性需氧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
化脓性葡萄球菌
肺炎葡萄球菌
粪肠球菌
屎肠球菌 革兰氏阴性需氧杆菌
大肠杆菌
流感嗜血杆菌
肺炎克雷白杆菌
乳糖变形杆菌
阴沟肠杆菌
粘质沙雷氏菌
醋酸钙不动杆菌
铜绿假单胞菌(绿脓杆菌)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厌氧菌
革兰氏阳性
产气荚膜梭菌
破伤风杆菌
脓毒梭状芽孢杆菌
难辨梭状芽孢杆菌
消化链球菌属
革兰氏阴性
脆弱拟杆菌
梭杆菌属
其他细菌
胞内鸟型分枝杆菌
结核分枝杆菌
星状诺卡氏菌
肺炎军团菌
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菌
真菌
烟曲霉菌,黑曲霉菌,土生曲霉菌,黄曲霉菌
皮炎芽生菌
白色念珠菌,光滑念珠菌,热带念珠菌
隐球菌,新型隐球菌
球孢子菌
牙生菌
组织胞浆菌
孢子丝菌
病毒
巨细胞病毒
EB病毒
乙型及丙型肝炎病毒
单纯疱疹病毒
人免疫缺陷病毒(HIV)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参考文献
黎沾良. 外科感染的防治:现状与未来.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0,20(1):11-12.
Leyr MM, Fink MP, Marshall JC, et al: 2001 SCCM/WSICM/ACCP/ATS/SIS International Sepsis Definitions Conference. Crit Care Med 2003, 31: 1250.
Angus DC, Linde-Zwirble WT, Lidicer J, et al: Epidemiology of severe sep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Crit Care Med 2001, 29: 1303.
Valles J, Relo J, Ochagavia A, et al: Community-acquired bloodsream infection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Chest 2003, 123: 1615.
夏穗生. 重视外科感染的预防和治疗.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4,24(6):321-322.
Dunn DL: The boological rationale, in Schein M. Marshall JC(eds): Sourece Control. A guide to the Management of Surgical infection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2003, p9.
Rozycki GS, Tremblay L, Feliciano DV, et al: Three hundred consecutive emergent celiotomies in general surgery patients: Influence of advanced diagnostic imaging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on diagnosis. Ann Surg 2002, 235: 681.
Baric PS: Mordern surgical antibiotic prophylaxis and therapy—less is more. Surg Infect 2000,1 :23.
TurnidgeJ: Impact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on the treatment of sepsis. Scand J Infect Dis 2003, 35: 677.
Martone WJ, Nichols RL: Recognition, prevention, surveillance, and management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Clin Infect Dis 2001, 33: S67.
Weiss CA 3rd, StatzCL, Dahms RA, et al: Six years of surgical wound infection surveillance at a tertiary care center: Review of the cicrobiologic and epidemiological aspects of 20,007 wounds. Arch Surg 1999, 134: 1041.
Perencevich EN, Sands KE, Cosgrove SE, et al: Health and economic impact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diagnosed after hospital discharge. Emerg Infect Dis 2003,9 :196.
Cohn SM, Giannotti G, Ong AW, et al: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 of two wou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dirty abdominal wounds. Ann Surg 2001,233: 409.
刘承训,董齐. 外科手术部位感染的围手术期处理.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4 年,24 (6):331-332.
Margenthaler JA, Longo WE, Virgo KS, et al: Risk factors for adverse outcomes after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appendicitis in adults. Ann Surg 2003, 238: 59.
McManus LM, Bloodworth RC, Prihoda TJ, et al: Agonist-dependent failure of neutrophil function in diabetes correlates with extent of hyperglycemia. J Leukoc Biol 2001, 70: 395.
Trick WE, Scheckler WE, Tokars JI, et al: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ep sternal site infection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00, 119: 108.
吴安华,任南,文细毛等. 外科手术部位感染病原菌分布.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5,2(15):210-212.
Russo PL, Spellman DW. A new surgical-site infection risk index using risk factors identified by multivariate analysis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 Infect Control Hosp Epidemiol 2002,23: 372.
Greif R, Akca O, Horn EP, et al. Supplemental perioperative oxygen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wound infection. N Engl J Med 2000, 342: 161.
Pryor KO, Fahey TJ 3rd, Lien CA, et al.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and the routine use of perioperative hyperoxia in a general surgical populat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AMA 2004, 291: 79.
Melling AC, Ali B, Scott EM, et al. Effects of preoperative warming on the incidence of wound infection after clean surger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01, 358: 876.
Grubbs BC, Statz CL, Johnson EM, et al. Salvage therapy of open, infected surgical wound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using Techni-Care. Surg Infect, 2000,1: 109.
Solomkin JS, Mazuski JE, Baron EJ, et al. Infectious Disease Society of America. Guidelines for the selection of anti-infective agents for complicated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s. Clin Infect Dis 2003, 37: 997.
任建安,黎介寿. 外科危重病人的感染与抗生素的选择.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1 ,21(4):204-206
申正义,王洪波,宋佩辉等. 外科感染常见菌群分布及致病菌耐药性监测. 中华外科杂志1998,36(12):729-731.
Solomkin JS, Yellin AE, Rotstein OD, et al. Protocol 017 study Group. Ertapenem versus piperaciliin/tazobactam in the treatment of complicated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s: Results of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mparative phase III trial. Ann Surg 2003, 237: 235.
Malangoni MA: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ertiary peritonitis. Am Surg 2000, 66: 157.
Golub R, Siddiqi F, Pohl D. Role of antibiotics in acute pancreatitis: metaanalysis. J Gastrointest Surg 1998, 2: 496.
Meier R, Beglinger C, Layer P, et al: ESPEN guidelines on nutrition in acute pancreatitis. European Society of Parenteral and Enteral Nutrition. Clin Nutr 2002, 21: 173.
徐海燕,王海军,刘颖珍等. 外科术后真菌感染分析.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6,16(4):389-400.
杨国山,杜斌,吴增安等. 外科危重病患者的抗生素使用.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5,15(5):565-567.
Duncan CP, Beauchamp CP, MasriBA, et al. The antibiotic loaded joint replacement system: a novel approach to themanagementof the infected knee replacement. J Bone Joint SurgAm, 1992, 742-B Suppl III: 296.
Duncan CP, Masri BA. The role of antibiotic-loaded ce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an infection after a hip re placement [ J ]. J Bone Joint Surg Am, 1994, 762-A: 1742.
Bilton BD, Zibari GB, McMillan RW, et al. Aggressive surgical management of necrotizing fasciitis serves to decrease mortality: A retrospective study. Am Surg 1998, 64: 397.
毛一雷.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和SIRS.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6,26(12):921-923.
毛一雷,秦应之,宋琦. SIRS的抗细胞因子治疗现状,临床外科杂志,2004,12(11):719-720.
Malangoni MA. Necrotizing soft tissue infections: Are we making any progress? Surg Infect 2001, 2: 145.
Sawyer MD, Dunn DL. Serious bacterial infections of the skin and soft tissues. Curr Opin Infect Dis 1995, 8: 293.
National Nosocomial Infections Surveillance System. National Nosocomial Inf. ections Surveillance System(NNIS) report, data summary from January 1992 to June 2002. Am J Infect Control 2002, 30: 458.
Kollef MH. Treatment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Get it right from the start. Crit Care Med 2003, 31: 969.
Hoffken G, Niederman MS. Nosocomial pneumonia: The importance of a de-escalating strategy for antibiotic treatment of pneumonia in the ICU. Chest 2002, 122: 2183.
Menashe G, Borer A, Yagupsky P, et al.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n mortality of extended-spectrum beta lactamase-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isolates in nosocomial bacteremia, Scand J Infect Dis. 2001, 33: 188.
Bernard GR, Vincent JL, Laterre PF,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ecombinant human activated protein C for severe sepsis. N Engl J Med 2001, 344: 699.
唐伟松,李小毅,杨志英等,预防性抗生素在普通外科手术中的应用.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01,16(7):445.
Ely EW, Laterre PF, Angus DC, et al. PROWESS Investigators. Drotrecogin alfa (activated) administration across clinically important subgroup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Crit Care Med 2003, 31: 12.
Annane D, Sebille V, Troche G, et al. A 3-level prognostic classification in septic shock based on cortisol levels and cortisol response to corticotrophin. JAMA 2000, 283: 1038.
Annane D, Sebille V, Charpentier C, et al. Effect of treatment with low doses of hydrocortisone and fludrocortisone on mortality in septic shock. JAMA 2002, 288: 862.
Keh D, Boehnke T, Weber-Cartens S, et al. Immunologic and hemodynamic effects of “low-dose” hydrocortisone in septic shock.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3, 167: 512.
杜顺达,毛一雷,何桂珍。肠源性感染的新途经:淋巴免疫通道学说,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2,22(9):549-551.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Updated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s to HBV, HCV and HIV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MMWR 2001, 50: 23.
Goldberg D, Johnston J, Cameron S, et al. Risk of HIV transmission from patients to surgeons in the era of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J Hosp Infect 2000, 44: 99.